東北菜,八大菜系在逃笨蛋

當影視文藝作品和公共輿論中,東北越來越頻繁地以悲傷的落伍者形象出現,供人唏噓或嘲弄時,東北人對於笨菜的執著就顯得更為意味深長。
最早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東北人,其實最早領悟瞭“笨“的可貴。
作者 | 曹徙南
編輯|道喵嘰
題圖 | 圖蟲創意
天一冷,東北菜的主場就到瞭。
鍋包you、小雞燉me菇、地三鮮er……隻要念出這些極具地域特色的“咒語”,一盤盤沉甸甸的、分量十足的經典款,便會用它們滾燙鮮香的熱氣,安撫每一個因為天氣寒涼而傷感的味蕾和胃。

小雞燉蘑菇是一道傢喻戶曉的東北名菜。(圖/圖蟲創意)
中國八大菜系中唯一的北方菜,除瞭留下“九轉大腸”這樣的傳奇,還在東三省的冰天雪地裡早早埋下基因,成就瞭兼具異域感、工業風、山野氣的獨特地方菜系。
而趕在全國人民對於北方菜隻留下每年春晚上永不缺席的接頭暗號“包餃za”這般單調匱乏的刻板印象之前,東北菜又沖出瞭黑土地,於全國各省開枝散葉,用“舒芙蕾一般的”雪衣豆沙,無比硬核的小豬蓋被與大飯包,渾身網紅氣質的凍梨凍柿子……征服一眾新擁躉。

人生建議:吃東北菜一定要嘗一嘗雪衣豆沙!(圖/小紅書截圖@美麗桃桃冰)
都說東北人熱情,那東北人對於美食的熱情,哪怕是來自西伯利亞的風都無法吹滅。
長期作為中國八大菜系編外成員的東北菜,顯然已經有瞭要轉正的跡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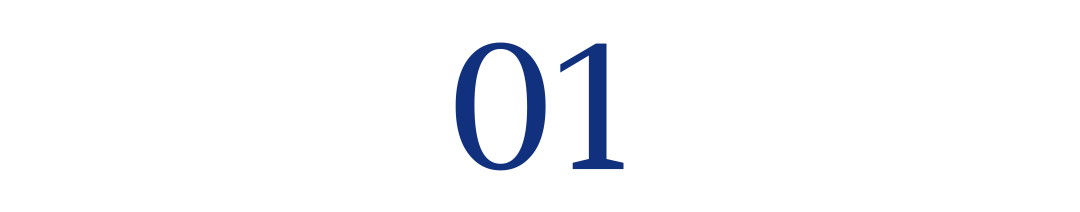
東北菜的混血基因
東北菜或者關東菜的稱謂,出現得相當晚近。東北菜作為一個整體被命名,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才在中國餐飲行業中出現並流行開來的——
這也讓東北菜少瞭很多歷史包袱,在其他菜系紛紛陷入原教旨主義內鬥的時候,東北人的飯桌上反而為各種飲食文化都留有一席之地。
闖關東時期,全國各地的移民帶著割舍不下的傢鄉味來到東北,過瞭山海關,便落地生根,四川麻辣燙就變成瞭撫順麻辣拌,東北大米做成的過橋米線更韌、更彈,牡丹江的煎餅餜子裡可以加烤冷面……

全國各地的移民帶來的傢鄉菜成就瞭東北菜的混血基因。(圖/《闖關東》劇照)
畢竟對於習慣直來直去的東北人來說,再正宗的菜,不好吃,那也是扯犢子。
除瞭魔改中國本土菜,東北人開放的味蕾也歡迎異域風味。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歐洲人、俄國人、朝鮮人、日本人紛紛湧入東北,使得東北地區成為整個東北亞大陸文化最為活躍的地區。與外籍人士一同抵達東北的,還有啤酒、面包、香腸。根據1937年的數據,僅哈爾濱的西餐廳就達260多傢。
在諸多的舶來飲食習慣中,北邊的俄國和東邊的朝鮮半島由於地緣因素,對東北菜的影響最為深遠。

東北朝鮮族的芝士年糕。(圖/圖蟲創意)
如今黑、吉、遼美食雖然以東北菜的名義組團出道,但三省的口味還是各有千秋。
其中最北的黑龍江,也保留著最濃鬱的俄式風情。比如現在作為城市名片之一的哈爾濱紅腸,又稱“裡道斯”,本來是俄國和東歐地區的常見美食,傳入東北後,在淡化原本的煙熏味道的基礎上,又多添加瞭一份蒜香。

哈爾濱紅腸分有不同口味。(圖/圖蟲創意)
除此之外,哈爾濱的罐菜也是典型的“中俄混血”食物,它更像是俄式紅菜湯和中式燉菜的結合體。
按照個人喜好,豬、牛、羊、蝦,乃至純素菜,都可以做成罐菜。以罐蝦為例,其做法是將新鮮的大蝦處理好後,裹上雞蛋液和面粉油炸定形,再放入小罐中,用調好的番茄湯底熬煮,最後加入芹菜、胡蘿卜調味。
甚至連黑龍江人吃的咸菜裡,都會多出一味俄羅斯常見的酸黃瓜,遇上東北菜的大魚大肉,反而成瞭下飯解膩的良配。

“俄”味有點重的哈爾濱餐廳。(圖/小紅書截圖@meme麼麼)
東依朝鮮半島的吉林,本就有朝鮮族聚居,這為東北菜吸納朝鮮美食元素提供瞭天然條件。
特別是在位於邊境地帶的延邊州,你絕對能吃到比首爾還地道的朝鮮美食。朝鮮美食喜歡生拌、生漬、生烤。韓國人引以為傲的泡菜文化,到瞭東北人嘴裡那就是漫長的冬季裡離不開的辣白菜。

辣白菜是中國朝鮮族的傳統美食。(圖/圖蟲創意)
裝菜喜歡用盆的東北人,更是將朝鮮族標志性的涼拌菜升級為東北大拌菜,各色蔬菜、豆制品和精制碳水,可以配麻醬,也可以配醋和糖做成酸甜口。
東北人用實力證明,沙拉難吃,絕對是白人的問題。

老工業基地的遺產,硬菜
“硬菜”一詞源於東北話,可以理解為西餐裡的主菜,通常指那些端上來就感覺要誘發心腦血管疾病的大菜。就像廣東人下館子一定要點一盤青菜,東北人請客吃飯必須整兩個硬菜。
如果隻能用一個字概括東北菜,的確也找不出比“硬”字更恰當的瞭。可以說東北菜裡隨便一道傢常菜,放到外地去,絕對都算得上硬菜。

東北醬大骨是東北菜“硬”的直觀體現。(圖/圖蟲創意)
在東北點菜,你首先要學會聽懂老板的弦外之音。對於你呈上的菜單,如果老板的評價是差不多,那就是這桌得扶墻出去。如果是吃不下,那意思就是要“吃不瞭,兜著走瞭”。如果是太多瞭,那後面三天的飯都有瞭。
分量大就算瞭,關鍵肉還多。由於持續近半年的寒冬,東北地區的果蔬選擇本就不多。當然,“沒菜吃才吃肉”隻是東北人的自我調侃。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東北遙遙領先的不隻是工業化。其飲食結構變化還得歸功於東北的城市化進程,在全國人民還要為吃肉精打細算的年代,東北人已經提前實現瞭吃肉自由。
即使是在食品冷鏈和物流水平都能夠保證新鮮果蔬供應的如今,肉多菜少的特點仍然在東北菜中得以保留。

鐵鍋燉。肉是東北菜的靈魂。(圖/圖蟲創意)
2016年,東北三省人均肉類消費量達到89.5公斤,超出全國平均水平32.5公斤。2021年的調查則顯示,東北人對於畜禽肉的日常攝入量達到60.12克,更有28.96%的人超標攝入。
除瞭分量和食材,東北菜的烹飪手法也相當“硬”。
除瞭不太講究食材處理的亂燉,東北菜還偏愛油炸。在東北,連代表性素菜地三鮮也是要過油炸一道才最正宗,飯後甜點拔絲蘋果更是重量級。
雖然江浙菜以對於糖的使用聞名,但若論及對於甜味的熱愛,東北菜不遑多讓。無論是燒烤,麻辣燙之類的小吃,還是正經的東北菜,在咸、酸、辣之下,總能藏著一絲回甘。

東北烤肉沒人不愛。(圖/圖蟲創意)
今天想要去東北體驗硬菜,最合適的地方其實不是飯店,而是街邊的盒飯點。
自助盒飯是東北最常見的快餐,基本以葷菜數量定價,素菜和米飯往往作為附贈。十來塊錢就能在幾十個滿滿當當的金屬菜盆中隨便挑選。鍋包肉、溜肉段、地三鮮、柿子雞蛋、燒茄子,都是飯盒中的主角。
東北盒飯的流行脫胎於曾經的東北大食堂,現在還有不少盒飯店的老板就是當年單位食堂裡的大師傅。盒飯當然說不上精致,但光是現炒、便宜、量大、下飯、熱乎、快捷這幾個優點,便足以擊中厭倦瞭高價預制菜的人們。

東北盒飯好吃且便宜。(圖/小紅書截圖@小曹與輝哥)
最重要的是,在東北硬菜裡,食客總能吃到久違的煙火氣。那是一種關於傢的柔軟,也正是這種柔軟,讓東北人得以度過那些漫長的季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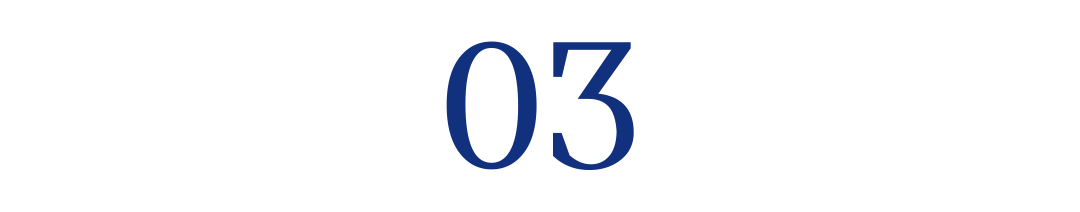
城東北人的飯碗裡,
全是“笨東西”
參照今天講求低糖、低脂的膳食觀念來看,東北菜簡直是在健康飲食四個字的雷區上跳舞。既然管不住嘴,另辟蹊徑的東北人就從食材上下功夫。“笨菜”,就是東北人在吃飯這件事上的馬奇諾防線。
“笨”作為形容詞,隻有在兩種情況下表示褒義:一是情侶間的打情罵俏,二是東北菜市場。
“笨”在東北的意思近似於歐美超市中常見裡的有機食物,但使用場景更為廣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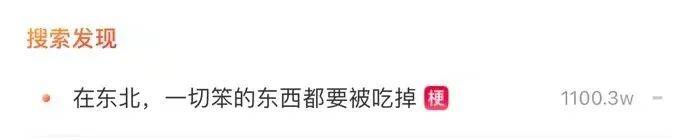
全國網友時刻關註東北人的餐桌,把笨東西也送上瞭熱搜。(圖/社交媒體截圖)
笨雞、笨鵝、笨豬,表示牲畜是自然散養,喂的是糧食,而不是標準化的飼料。笨土豆,笨茄子,笨玉米,表示種植過程中沒有施加化肥,用的是農傢肥。笨大醬、笨豆包、笨豆油,則是告訴你,其制作過程使用的是傳統手藝,沒有化學添加。

東北大豐收,食材簡單,營養豐富。(圖/圖蟲創意)
如果一定在當下的語境中給出一個通俗易懂的解釋,那麼“笨”就是科技與狠活兒的對立面,是東北人的鄉土情結,也是東北“物我兩安”的飲食傳統在當代的遺存。
地廣人稀的空間特點允許東北形成瞭單純“靠天吃飯”的經濟模式。稀薄的人口密度配上廣袤且物產豐富的土地,使得東北人的飲食得以高度依仗於自然的饋贈。
不似中原以及南方等人口稠密區的精耕細種,多民族聚居的東北地區形成瞭以畜牧、狩獵、漁撈為主,以采集和種植為輔的生產方式。

東北地區多以狩獵、漁撈為主的生產方式。(圖/unsplash)
在南方農民還在為一畝田能多產幾石糧食而“汗滴禾下土”的時候,東北人正在山林裡打獵、采野果子吃。
直到20世紀中葉以前,在東北的大部分地區,“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裡”都並非一句誇張的修辭,而是人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日常。
無論是菜市場還是在飯館,隻要用的是“笨菜”,價格就會比普通食材高出一些,仍然相當受歡迎。“笨菜”可不是專門賣給笨人的智商稅,正如那句“最高級的食材隻需要最簡單的烹飪”,大開大合的東北菜是檢驗食材質量的最高標準。

土豆茄子去皮,加入青椒翻炒,再加入其他佐料就可以制作出美味的地三鮮。(圖/圖蟲創意)
笨雞蛋滑嫩、笨豬肉緊實、笨豆芽爽脆,“笨菜”雖然在營養價值上和普通食物沒有拉開明顯差距,但在口感上卻是一筷子就能分得出來。
當影視文藝作品和公共輿論中,東北越來越頻繁地以悲傷的落伍者形象出現,供人唏噓或嘲弄時,東北人對於笨菜的執著就顯得更為意味深長。
最早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東北人,其實最早領悟瞭“笨“的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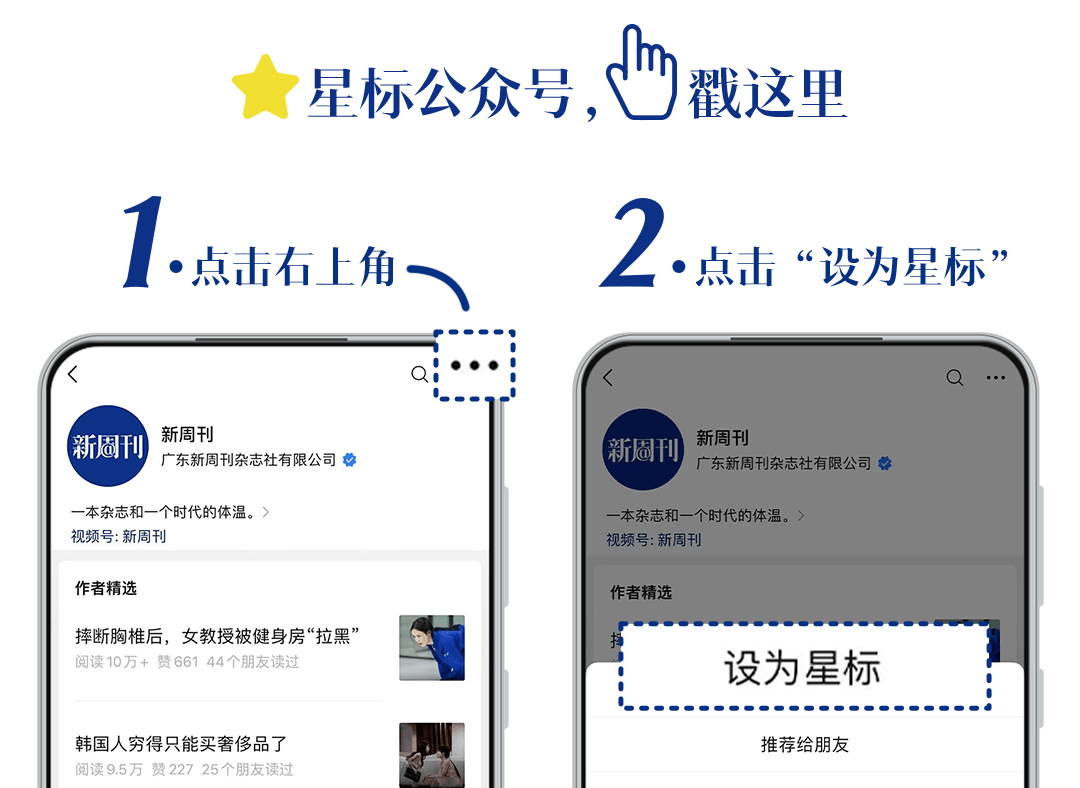

讀完點個【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