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赞 | 不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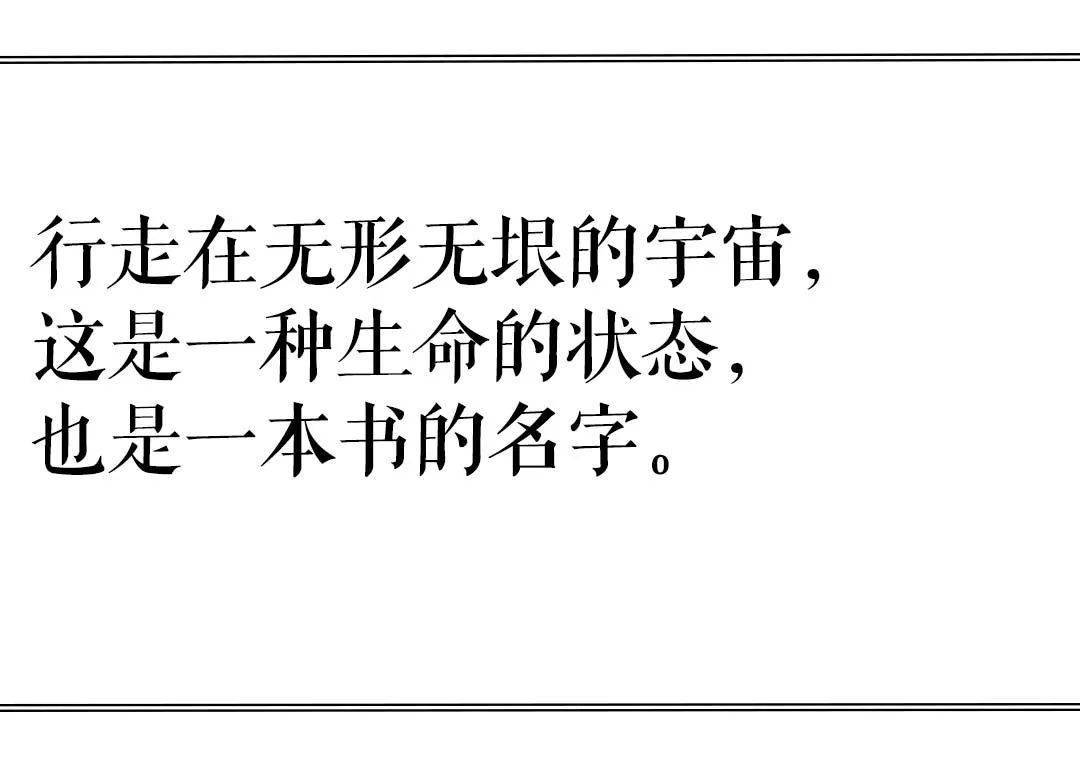
得知要去松赞百巴营地时我没有什么预想,自然给了什么,那里就是什么。最好,不要让我缺氧。只有一件小事我将要去实现:放一本《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在营地的书架上,混在书堆里,然后无人知晓。

这是一本最近刚发布的书,关于一位女雕塑家的自我以及她与学者们的对谈。我莫名觉得她选择在此时此刻来完成这本书,是在实现对自己和爱人的一个交代。生命有时候就是这样:本来你什么事都没有,刹那间你不得不上。所以,我要带它走:都市经常太挤了,我要把这个宽阔的思想与灵魂交给一片广阔的土地。 是的,旅行可以是一场放生。


人们说旅行是为了忘记自己,短暂的忘记自己的身份和故事。如果有一个地方还可以让你忘了之前的温度、湿度以及海拔,是不是听起来会不同。松赞百巴帐篷营地可以给你新的故事,或者一副新的体表。比方说我,一开始的晚上我总觉得好冷。有一个夜晚我想通了,我不管了,我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藏族舞。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觉得冷过。


营地的帐篷里没有提供电视。这是一件好事,说明这里足够自信。这在无声地告诉我只有无聊才需要电视,松赞百巴相信自己和来者都足够丰富。一台品质很好的无线音响取而代之,可以拎着走也可以在房间里听。
电视和音响是不一样的隧道:一个把你向内吸引,收取你的目光和听觉,让你一时不好脱身;另一个把你向外牵引,听着听着还可以看书看风景,然后拎起它说走就走。

在一个暗夜,我拎着音响独自来到离帐篷不远的山泉边。左耳是山泉的响彻,不会停摆;右耳是已故钢琴家的琴键发出对宇宙的展望与追寻。我就处在这两者的中间:一边未来,一边古意。
如果以远处的雪山作为一个坐标来对应,我会感觉自己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白天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望着雪山看很久,夜里虽然看不清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雪山没有颜色,没有味道,没有欲望,没有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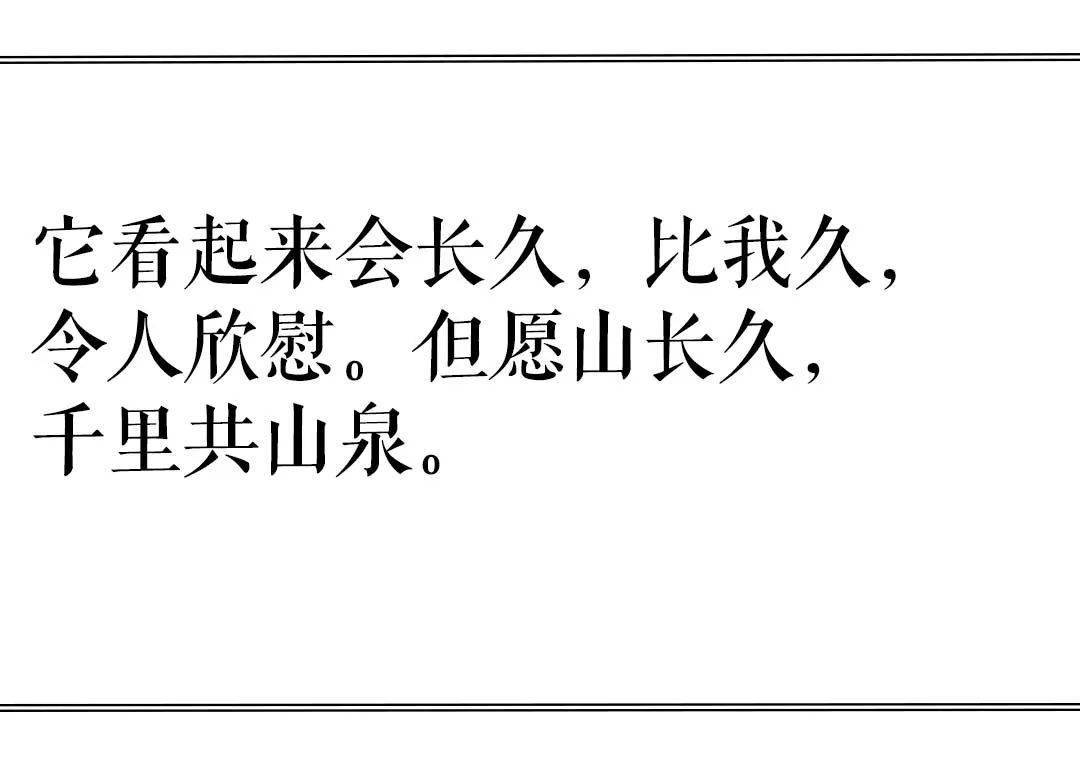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三月,德国艺术家约瑟夫·乔伊斯的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被击落,全身多处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说自己被当地游牧的鞑靼民族收留救治,他们往他的身上抹了很多气味刺激的牛奶以及奶酪,用毛毡和动物脂肪包裹住他破碎的身躯,以致于他奇迹般康复了。
这个听起来带着传奇色彩的事迹也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浑身上下暂时都没有毛病的我预约了一次SPA,我被一位和蔼的藏族女士抹了很多很多的精油。她跟我说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我呆呆地望着头顶的帐篷,发现帐篷的顶好高,好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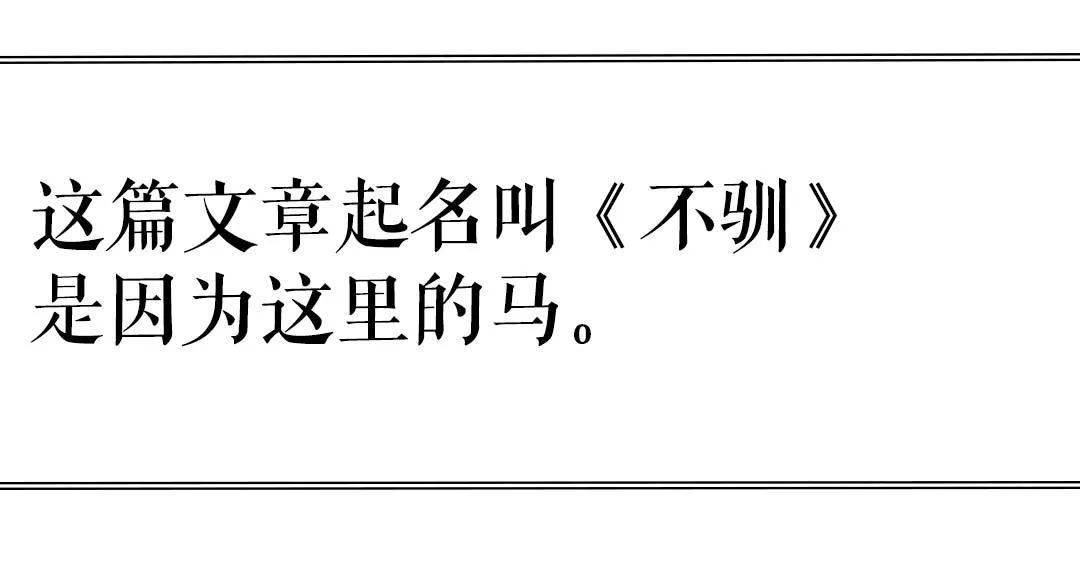

如果再晚一些走,我会花一天的时间只跟着一匹马。它走到哪我走到哪,它吃草我就啃面包,它找地方喝水我就找块石头坐坐喝可乐。
一个下午我在回帐篷拿东西的路上,听到短促而有力的马蹄声。两匹马在我前方五十米的地方跑了起来。那种有力的蹄声中带着一种良好的训练度,那种声音告诉我它们知道要往哪里跑,跑多久。它们知道可以如何跑得不影响到其他的人或马,这就是好马。



我看到这些马有很多的食物,一些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草。如果在一个地方马可以过的很好,人会更逍遥。我看到一张我坐在营地中的石堆上晒太阳的照片,看似随性摆放的石堆与树的枝杈,当我揣摩起来发现画面中的第一块石头估计需要六个人搬,第二块石头得四个,第三块石头可能是三个人,那棵横着的木段已经不是几个人可以搬运的事情了。 总之,让我们看到的不经意,都存在心思和气力。
有一匹小白马叫“土哥”,我们邀请驯养它的松赞人鲁茸向巴写了一段关于土哥的故事。虽然我们的文字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异曲同工。
土哥成长记
我叫“土哥”,彩云之南是我的出生地,所以我是一匹纯正的“小滇马”。别看我小,曾经的茶马古道上都是我们的身影。在香格里拉这片神奇的大地上,我可是涉足过广袤土地的香格里拉小马哥。
2023年是我来到这个星球的第九年,有一天我在草原上快乐奔跑,与我的第一任主人相识,从此我踏上了“马术之路”。我教学过很多很多的小朋友,每当有人叫我“土哥”的时候,小马蹄总是会不听使唤地朝着声音的方向奔跑。后来我成为了松赞的一员,开始了我的更高标准的成长之路。松赞每天有我很喜欢吃的草料和胡萝卜,那可真是太让我开心了。
这里有更多的马星人,我们和大家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那些日出时的快乐奔跑,那些夕阳下的美好回忆,让我在这个大家庭愉快地成长。
有一天,师傅让我去外面看看,于是我来到了西藏林芝“松赞百巴帐篷营地”,我将在香格里拉的丰富马术经验带到了松赞百巴,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这里体验,慕然回首我已经是这里的“明星”教师了。这里有雪山、有河流、有峡谷,都是我可以带您前往的目的地,这里还有很多我的其他小伙伴,希望下一次可以与您在百巴相遇。我是土哥,我在松赞百巴帐篷营地期待您的到来!
那天早晨我看到工作中的藏族女性们把从帐篷中收拾出来的枕头和被套扛在肩膀行走在草地上,很日常,也很像一种传统的仪式。她们的脸上不是辛劳,是从容安定还有幸福。这让我想起我在那里拍的两张照: 马背和远山是一回事,没有谁要去驯服谁。

撰文、摄影:庄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