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零食的“扛把子”在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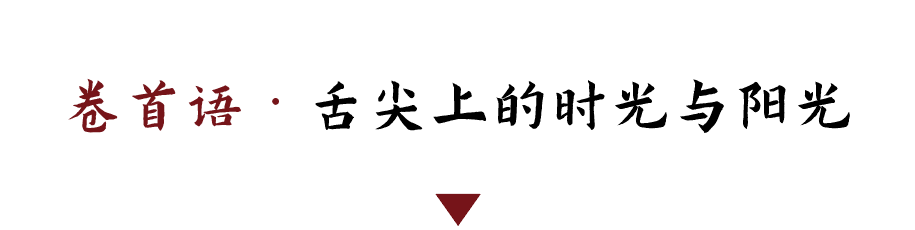
立冬之後,
南方享有難得的“小陽春”,
曬、烤、醃制……
人們雜糅瞭時光和陽光,
將收獲的新鮮果蔬制成各種零食,
以度過漫長的冬季,
迎接登門閑談的客人和春節的到來。

很難去追溯一道鄉間零食的起源,
制作工藝並不復雜的零食中,
除瞭蘊含人們對於吃的執著和智慧之外,
更多的是長輩們對孩子的耐心和愛。
光是一種紅薯,
聰明手巧的農人就能切片、切絲、搗成泥;
或油炸、或蒸煮、或晾曬;
做成糖水紅薯、紅薯幹、
紅薯糕、玉蘭片、麥芽糖……
這些變換瞭形狀、味道的農傢作物,
為我們編織瞭一個香甜的童年。

兒時的春節,
挨傢挨戶去拜年,
用父母教的吉祥話,
換取一大堆花生、瓜子、紅薯幹等零食,
如果偶爾有一塊柿餅、法餅,
那就能歡天喜地一整天。
長大後,依舊鐘情於零食,
不過卻難以找到兒時那份
留在舌尖舍不得吞咽的幸福感,
因為那時零食難以獲取而格外珍惜,
也因為鄉間零食裡,
有時光和陽光的沉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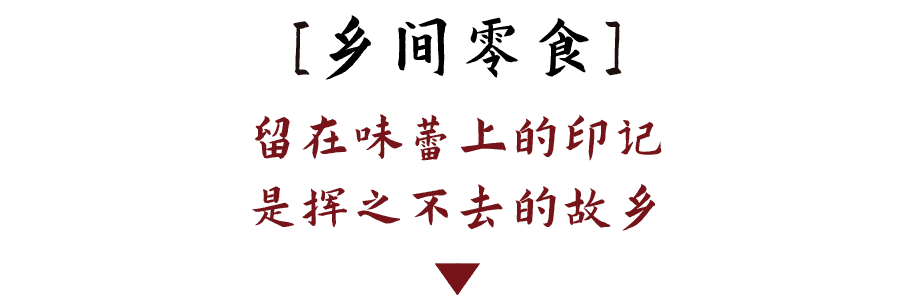

11月,在一片暖陽裡,我們找尋鄉間的零食,找尋那些曾經慰藉我們童年的甜與香、酸與辣。
那些最鄉土、最純粹的鄉間零食,是我們鄉愁的安放之所,也是我們揮之不去的故鄉烙印。
湘西最有名的零食是酸菜,紅心蘿卜醃制之後,加上一層油辣椒,是湘西人最熟悉的美味。在懷化,幾乎每傢每戶都有一個酸菜壇,其實,酸菜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零食,隻是現在物質充裕,將其當作零食,也是自然的事情。在舊時的湘西、湘南,才舍不得把菜做成零食呢,不下飯,就是一種浪費,所以湘西、湘南多以醃制為主,酸辣椒、水豆豉、醋蘿卜等醃制蔬菜,是人們的生活智慧。而在生活水平提高以後,這種留在味蕾上的印記,才成為人們鐘愛的零食。
不適於做菜的果實,才會做成果脯,是難得的零食,比如紅薯。

紅薯片。
在整個湖南,紅薯片、紅薯絲、紅薯幹,或炸或曬,工藝都大同小異。瀏陽更是把紅薯用到瞭極致,加入各種果脯制作中。
瀏陽無疑是湖南最會做零食的城市,他們把常見的果蔬都能做成零食。蒸、煮、曬,是主要工藝。編著《湖南地理志》的傅角今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去到瀏陽,對瀏陽的總結是“農作物以米為主,其餘麻、高粱、番薯、果品、茶及茶油,亦甚多”。有足夠的物資,才會敢於把蔬菜當成零嘴。

炸紅薯幹。
在零食的制作上,瀏陽似乎遠離長沙,更親近江西。在瀏陽市南市街做炒米糕生意的蔣冬生就把江西當成炒米糕手藝的發源地,常從江西引進新的產品。
不過豐厚的物產,並沒有讓瀏陽人變得揮霍,反倒在零食中窺見他們的節儉,剩飯做成炒米,紅薯藤曬幹做成酸菜,酸棗的核也能做食品……鄉間零食,在某種意義上比菜肴更能反映地域性格。
麥芽糖、桂花糖、柿餅、皮豆……
湘西這個制糖村慰藉瞭幾代人的童年
麥芽糖,大概算不得南方的特產,湖南不產麥子。不過,麥芽糖卻藏在南方的童年記憶深處。村口、巷子裡,挑著貨郎擔的賣糖者並不高聲叫賣,隻是用兩塊鐵片敲擊出“叮叮當當”的聲響,麥芽糖也叫作“叮叮糖”,這是與孩子的默契,孩子們聽到聲響,就拿出積攢瞭許久的啤酒瓶、牙膏殼、塑料,換一塊麥芽糖,含在嘴裡,久久舍不得咀嚼。
而我們這次鄉間零食的找尋,也正是從麥芽糖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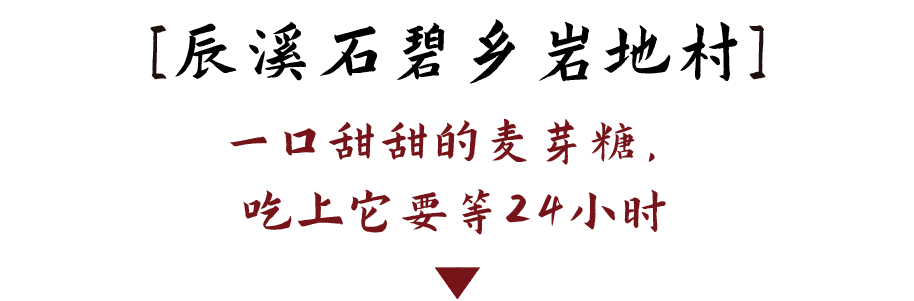

11月1日,辰溪縣石碧鄉巖地村唐長青傢熬制的麥芽糖,“需要24個小時”。
11月1日下午三點,我們趕到辰溪石碧鄉巖地村時,制糖人唐長青已經熬完瞭當天的最後一鍋糖,在墻角的一個木樁上拉糖。
“有一百多年歷史瞭,聽說是一個外地人來到我們村教制糖,後來幾乎傢傢戶戶都做麥芽糖,不過現在隻剩下七八傢瞭。”村裡人說不清這裡的制糖業是從何時開始,但卻隱隱感到瞭這個行業的危機。“太辛苦瞭,年輕人都不願意學。”盡管制糖收益不錯,卻也難以留住年輕人,唐長青傢三代制糖,但他的兒子不願意繼承祖輩的手藝,在外打工。
制糖的確是辛苦的,制糖人的一天從凌晨三點開始。
11月2日凌晨三點,唐長青起床,前一天準備好的麥芽拌上碎米的原料已經發酵好,倒入熱水,導出來的就是糖水瞭。唐長青將糖水倒入熬糖的鍋裡,加入少量的菜油,“放些菜油不會粘鍋。”唐長青解釋,小火將糖水熬制成麥芽糖需要八個小時的漫長時間,等待的時間裡,制糖人並不能走開,需要不時查看火勢大小。

唐長青查看火候,爐火映紅瞭臉,他說,最難熬的是夏天,熱得不得瞭。
“這個季節還好,夏天熱得不行。”唐長青往灶裡加炭,爐火熊熊,這時我們才註意到作坊裡有一臺巨大的風扇,看來在悶熱的夏季,待在這裡頗是一種煎熬。
熬糖的灶是三孔長灶,連接著發酵池和熬湯鍋,中間是一口燒熱水的鐵鍋。在熬糖的日子裡,蒸煮碎米、發酵、熬糖,爐灶24小時不斷火,“發酵要燒火,不然會變酸。”當糖水裡的水分蒸發得差不多時,變得濃稠起來,需要不停攪動,避免糖被燒焦。攪棍的是“T”字形的木制工具,唐長青不時將攪棍提起旋轉,被帶出的糖在鍋裡形成一個透明清亮的氣泡,他以此來檢驗糖的成色和水分。“要等水分全部蒸發掉。”經過幾個小時的漫長等待,第一鍋麥芽糖終於出鍋,唐長青熄瞭火,將糖迅速盛出,動作稍微慢些,就會黏在勺上。“其實,拉糖是最累的,需要力氣。”麥芽糖冷卻瞭幾個小時後,才能上樁拉糖,唐長青前進後退,幾十公斤的麥芽糖在手上拉伸聚攏,像是一場舞蹈,金黃色的麥芽糖也逐漸變成瞭潔白模樣。
麥芽糖的制作過程,多半時間都在等待裡,等待麥子發芽、等待發酵、等待熬糖、等待冷卻,“蒸米三個小時,發酵八個小時,熬糖八個小時,再加上拉糖、拌料,一鍋麥芽糖完成大概需要二十四個小時。”

唐長青將麥芽糖從糖鍋內舀出,等待冷卻。
唐長青習慣瞭這種漫長的等待,令他欣慰的是,他在這個村莊裡24小時的等待和勞作成果,很快就能到達遠方,慰藉某個素不相識的味蕾,“我的麥芽糖都是發往長沙、廣西、廣東、重慶的,光是在長沙,就有一百多人在等我的麥芽糖。”這個被等待打磨得無比沉靜的漢子,臉上露出瞭一絲驕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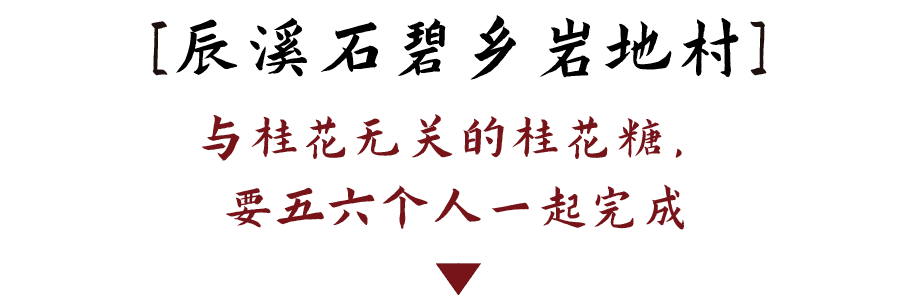

巖地村最鼎盛的時候有七八十傢制糖作坊,“村裡的井水都不夠用,要翻過山、走上幾公裡路去別的地方挑水。”唐長青的母親張蘇翠講述著巖地村曾經的熱鬧。制糖業興盛時期的巖地村,不僅做麥芽糖,也做飴糖和桂花糖,飴糖濃度較低,是糖類糕點不可少的原料;桂花糖其實與桂花無關,是濃度高的麥芽糖拉制成的中空的節狀糖,工藝復雜。
“要五六個人一起做才能完成。”唐明儒和父親是村裡少數幾個掌握瞭制桂花糖技藝的師傅,但他早已不再制糖。沉淀瞭這個傢族幾十年的制糖時光,用來舂麥芽的石臼也已擱置在傢門前的路邊。“太辛苦瞭。”唐明儒直言。
不過談起做桂花糖,唐明儒依舊興奮,“做桂花糖要求糖的濃度高,糖放在嘴裡要像硬糖一樣甜、脆。”傳統工藝總是難以量化,全憑手藝人的經驗,唐明儒特意從傢裡拿出一顆硬糖來演示對比。濃度高的麥芽糖容易硬化,要將其做成中空的節狀,這是桂花糖最難的工藝。傳統的軟化糖的設備,是用來熬糖的甑,在鍋裡加上水,燒開,升騰的蒸汽能夠讓糖始終保持適度和軟度。

“蒸汽太過,容易把糖融掉;不夠,又不足以軟化。”拉糖、切糖、上芝麻的各個環節都不能離開蒸汽,沒有一定經驗的師傅很難把握蒸汽的火候,“做桂花糖比做麥芽糖辛苦,而且需要的人工多,所以村裡很多人不做,甚至不願意學。”
桂花糖的成品脆、甜,“利潤大概是麥芽糖的兩倍。”不過如今村裡已經無人再做桂花糖,顯然,利益早已不是傳統手藝存在的唯一條件。巖地村制糖人們每天凌晨三點起床的勞作方式,艱辛原始的制糖工藝,讓人難以堅守。
老手藝人的退出,年輕人的逃離,這個古老的制糖村落,似乎早已無力承載過多繁復的工藝。但值得這個村莊驕傲的是,他們堅守的“甜”,慰藉瞭幾代人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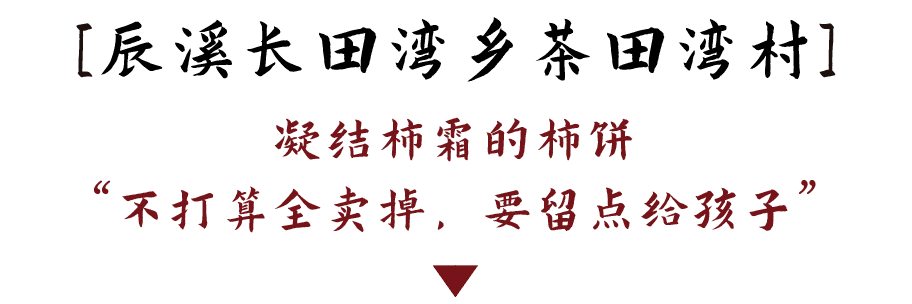

辰溪長田灣鄉茶田灣村的老柿子樹,據說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
沈從文在《沅水上遊的幾個縣份》的文章裡寫道,懷化鎮過去二十裡,“再過去二十五裡名‘榆樹灣’,地方出好米、好柿餅。”榆樹灣如今早已是城區,那裡的“好柿餅”自然也無處可尋瞭。不過沈從文筆下的“好柿餅”還能在辰溪長田灣鄉找到,那裡的甜柿,味甜多汁,適宜於做柿餅。
傍晚時分到達長田灣鄉茶田灣村,迎接我們的是村口一棵柿子樹,隻剩下光禿禿的樹枝,幾個高處的柿子得以保存下來,在夕陽裡顯得格外紅。村民們說,那棵柿子樹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這樣的柿子樹在村子裡多處零星散佈。
“你們要是早來半個月,我們就正好在摘柿子。”茶田灣村的村民唐清明正將晾曬在外面的柿餅收回傢中,他傢的柿餅已經晾曬瞭半個月。唐清明傢有十幾棵柿子樹,“前幾年可以收一千斤柿子,這幾年不行瞭,柿子樹結得果子越來越少。”他把原因歸結於柿子樹蟲子太多,而柿子樹太過分散,“殺蟲太麻煩,索性就由它去。”往年他都要到集市上才能賣完傢裡的柿餅,今年收獲的柿子不多,上門的顧客就可以消化。

“霜降之後的柿子做成柿餅才好吃,不澀。”霜降吃柿子是村裡的習俗,吃柿子可以禦寒保暖,而多餘的柿子就做成柿餅。
做柿餅的工序簡單,柿子的選擇是關鍵,“削皮,然後就是晾曬,如果沒有太陽還得用火烤。”唐清明傢今年的柿餅就用火烘烤過,還有些許煙火的味道。“用手捏柿餅成形有講究,一般要捏三遍,隔幾天捏一次,要把果肉的硬塊捏軟,不能破壞表皮,慢慢地把柿子用手壓成餅狀。”柿餅成瞭形,晾曬半個月,隨著水分蒸發,會在表層凝結成一層柿霜,“有柿霜的柿餅口感清甜,最好吃。”唐清明熱情地讓我們嘗嘗他傢的柿餅,今年柿餅的價格不錯,他卻不打算全賣掉,要留一些給在外打工的兒女。

瀏陽亦多柿子,在茶田灣村的柿子已經成熟掉落,隻剩枯枝時,瀏陽的柿子樹卻依舊枝繁葉茂,柿子沒有完全成熟,山上的野柿子樹掛滿果實,卻無人問津,“吃柿子容易得結石”的說法似乎成瞭瀏陽人的某種共識。也有人不信那種說法,料理柿子的方法遠比茶田灣村隨意,隻是削皮、晾曬,或者切片晾曬,瀏陽人認為直接晾曬的柿子味道比柿餅還好。


在瀏陽的飯店,炒米是不可少的飯前點心。去鄉間做客,主人會拿個塑料瓶,往你手裡倒滿炒米才能表達他的熱情。瀏陽不少人還保留著將剩飯曬幹制作成炒米的習慣,這種勤儉裡的創造,大概就是炒米的由來吧。
而將炒米用糖粘合,加入糖的甜味,切成塊狀,就成瞭炒米糕,香酥松脆,是孩子們熱衷的零食。蔣冬生在南市街的一個簡陋門面上做炒米糕生意已經多年,那個不大的房子既是作坊也是門面。門口擺放著各種炒米糕,芝麻糖,凍米糖,一個大油鍋,加上一口熬糖的小鍋,門前一塊案板,就串聯起瞭炒米糕的全部生產流程。
糖鍋在我們到達之前已經燒上小火熬糖,“這是飴糖加白糖,飴糖粘性好。”蔣冬生不停攪動著沸騰的糖水,另一口盛植物油的大鍋則是用來炸制米粒和南瓜。
最傳統的工藝遠沒有這麼奢侈,多為炒制工藝,將米與細沙混在一起炒,使米膨化。炒制工藝固然節約成本,卻容易將細沙混入食物。如今甚至省去瞭膨化的工序,可以“直接從江西拿半成品。”

蔣科用木滾筒將米壓平平。
糖熬制完成後,需要將炒米或凍米倒入糖鍋中攪拌,讓米和糖均勻混合。蔣冬生的侄子蔣科,迅速將混合物倒入案板的木架內,用木滾筒加滾平,切成長條。撤去木架,再切成小塊,這項工作蔣科已經做瞭四年,不用比劃,隨著有節奏的起落聲響,米糖就被切成瞭均勻大小的小塊。
“我們小時候吃得最多的是炒米糕和凍米糖,現在種類越來越多瞭。”在炒米糕市場裡摸爬滾打20多年,蔣冬生守護著最初的味道,店鋪也開始引進新的品種,“南瓜糖是前兩年才從江西引進的,不過,還是炒米糕和凍米糖賣得最好。”
+
與自然時序同呼吸
文字|唐兵兵
圖片|盧七星
微信編輯|方遠親(實習生)
往∣期∣回∣顧
湖湘地理招合作攝影師
湖南最權威銀杏觀賞指南
